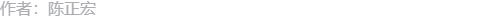李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,是他永远有梦的理想主义底色。他青年时代写的《上李邕》里,已经自比能腾飞九万里高空的大鹏,说——
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溟水。时人见我恒殊调,见余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最后两句,借孔子“后生可畏”,直白地告知诗作的受赠人、当时的渝州刺史李邕:“您可别小看我这个小年轻啊!”
直到他62 岁写《临路歌》,那只曾在年轻时翱翔于心中的大鹏,依然倔强如故——
大鹏飞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。馀风激兮万世,游扶桑兮挂石袂。后人得之传此,仲尼亡兮谁为出涕?
《临路歌》是李白在病重之后精力不济的情况下完成的最后作品,当是绝笔。诗人以大鹏自比,浩叹一生壮志未酬的悲怆,虽已不能如当年那般神勇潇洒,趁风少歇,就能把沧海之水一扫而空,却依然有不服输的韧劲。事实上,读李白的作品,晚年不乏消沉的东西,但激情和梦想从未离开。这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,一股跟那种总是被规矩所束缚的陈腐之气很不一样的清流。
当然,也毋庸讳言,李白永远有梦的理想主义,在现实面前时常是敌不过个人的功名欲望的。他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里写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,重点原并不在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——如果有机会,再匍匐在贵妃的石榴裙下,写几首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也是无妨的——重要的,其实是“开心颜”。不光脸上开心,心里也开心,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开心,则搞什么事都没意思。尤其是心里不开心,还要强颜欢笑,那是最最没意思的。在那样的场景中,太白的境界,才会灵光乍现,突然爆发,才会掀桌子:“老子不干了!”
清代学人龚自珍曾有一个说法:“庄、屈实二,不可以并,并之以为心,自白始。”意思是庄子和屈原,其实是不同的两家,不能混在一起的;把庄子跟屈原合二为一,并且视这种合一为一种心灵的聚合,是从李白开始的。我们理解,龚自珍之所以要先把庄子跟屈原分为两家,是因为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,而屈原则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;理想主义者的坚守,跟无可无不可的绝对自由,是有冲突的。到了李白那里,追求身心的自由和至死不灭的理想主义,两种看起来不无抵触的理念融合了:他把个人的身心自由,外化为简洁明了的“活着要开心”,并视此为一种可以抵达终极理想的途径。
唐代以后的中国人,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多了很多限制,中庸意识弥漫于社会各阶层。不过无论如何,在中国人的内心,一直给李白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。他固然比不上杜甫那般沉郁深刻,也不像白居易这么平易近人,但是,在用自己的神来之笔,诗意地表达人既应该有高远的理想,也应该活得自在开心方面,他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。
(摘自《环球人物》2024年第11期,本刊有删节,张云开图)